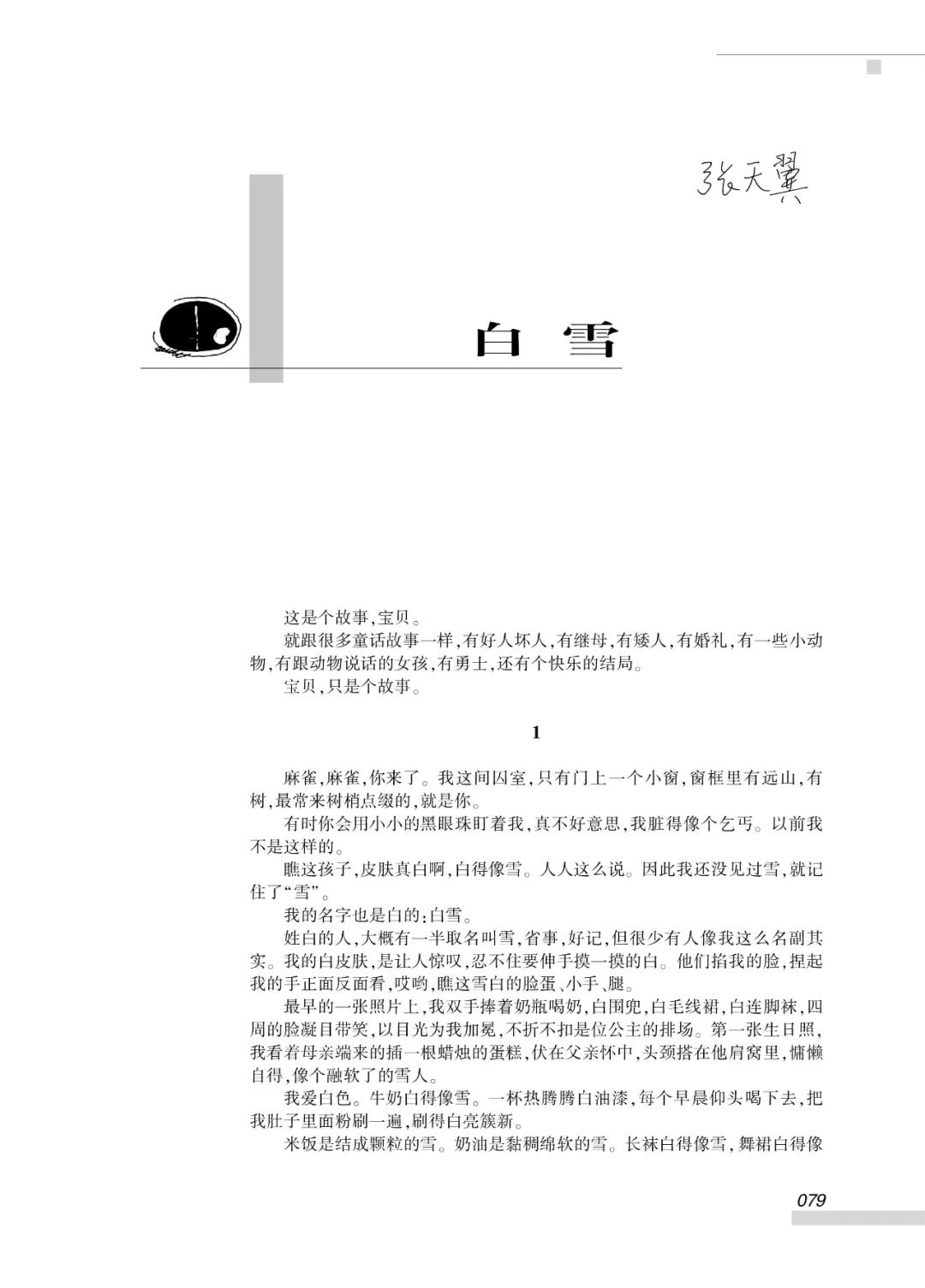作者:小葡萄
编辑:米洛/屋鸦
短篇小说《白雪》是对格林童话《白雪公主》的再次创作。从小说开篇起,作者张天翼一再强调这是一个童话故事。读者看到一个普通女孩白雪的成长经历,她在父母的注目中降生,在爱与珍视中成长,如同一位公主。紧接着母亲去世,继母出现。当我们和主人公一起猜想继母侯老师是否会像《白雪公主》中的皇后那样,显露出恶毒的面向时,故事却并未沿着格林童话既定的轨迹行进。继母待白雪始终很好,白雪在她的悉心照顾下,依然过着被关爱、呵护的平常生活。直到一次出于善意的帮扶,白雪被绑架拐卖,从此跌入深渊,进入铁链女的世界。
在这个故事版本里,小矮人的家不再是安全的庇护所,而是剥削和迫害女性的地狱。白雪被拐卖至此,从此生命割裂成两半。
小说的终章,作者再次提醒这是一个童话故事,黑衣人与白衣人如同勇士一般乘着飞车从天而降,带白雪公主逃离了矮人之家。至此,从被拐卖、禁锢到被解救,张天翼将铁链女等拐卖案件中女性所遭遇的一系列暴力情境完整呈现在了读者面前。童话与被拐卖被性侵犯的情节形成了鲜明对照,再次构成了对现实的反讽。
拐卖情节的再现
小说重现了许多拐卖案件的细节。白雪在火车站遇到一个窘迫的孕妇,她出手帮助,被带至一个偏僻的角落,随即被强制掳走。火车站是拐卖案件的多发场所。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高院2016年发布的《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调研报告》显示,广州拐卖妇女案件大多发生在火车站等处,并且被拐卖的妇女大都比较年轻,最小的仅15岁。有研究显示,14 岁以上的被拐卖者以女性为主,被拐去向通常是结婚或从事情色服务。此外,被拐卖儿童和妇女的去向基本都与父权文化下“身体和性别”这一核心有关,TA们可能会遭遇被绑架、拘禁、强奸甚至杀害等危险。
白雪被拐卖时即将上高二,年龄大概就在14、15岁左右。她到了矮人之家,身体遭到禁锢,不得不忍受虐待与暴力,成为一件性和生育的工具。忽然之间,她就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一个俘虏、一个奴隶。
小说近乎残忍地还原了白雪多次遭受性暴力的情景。其中写道:“我来的第二天,就被他们用了”。矮人之家六个矮人,三男三女,“五个人按住我,五马分尸的姿势。万事通说,猪脑髓!把腿分开,压实膝头骨,别让她弓起腿,不然蹬人可疼...哎,对了。” “双腿上感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那力气属于一个饿坏了的人,急着掰开一次性筷子。两条时针分针,由锐角至钝角。零点,几秒钟就走到1点55,1点47,2点50。” 白雪成为一个受孕的容器,被矮人们轮番使用。她青春稚嫩的身体脱离主人的意志,开始怀孕,分娩,诞下死婴,又诞下女儿白荷花。在淤泥中孕育的白荷花,是第七个矮人,她的存在是白雪被剥削的命运里无奈的句点。
气味、痛觉、施暴者粗暴作呕的话语,与白雪的内心活动贯穿全程,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全都呈现于纸面,读者仿佛亲眼目睹罪恶在眼前发生。当身体与心灵备受摧残,白雪只能靠想象着被解救、重回父母身边来捱过当下。她无数次回想起曾经的玩伴、老师、父母、外婆,还有诗文、小说、数学题,这些过去生活里的人和事宛如一场旧梦,提醒着我们,随着白雪被禁锢得越久,她离一个普通中学生的生活就越远。
被拐卖后白雪生活的环境几乎与最初视频中铁链女的环境如出一辙。视频中的小花梅锁在大房子旁的一个破屋中,她衣着破败、食物糟糕。矮人之家的囚室里,白雪吃饭、喝水都在床上,排泄也在屋内,从小爱干净的白雪最初来月经时不想弄脏裤子,宁肯光屁股,她想要在被解救时保持体面。经血打湿褥子,干了又湿,屋子封闭,只有门上一扇小窗,气味散不去。白雪被囚禁的时间越来越长,她的头发数月未洗、衣服袜子还是来时那一套。透过村里男孩对她的窥视,我们得知她成了村民口中的疯子,只是因为她被拐卖被囚禁,因为窘况中想要保持最后一丝体面而裸露的身体,因为对自由的渴望与对自己境遇的绝望,因为爱与小动物交流的那颗纯真的心。
还有牙齿。小花梅牙齿零落,官方通报中提到,铁链女的牙齿脱落经诊断是重症牙周病所致。在白雪的故事里,她“从小被严格监督,天天刷洗,初三戴了一年牙套,矫正出一口齐剁白牙,个个坚固,没一个龋齿。”但在她受到暴力反抗后,牙齿离她而去:“万事通戴着棉纱手套, 开我的嘴,瞌睡虫操作钳子。 ......牙根在牙床里搅动,拧转,倏地离去,像撬开一个啤酒瓶盖,血咕噜噜涌出来,倒灌进喉咙。 ”
这其中,比喻无处不在。张天翼曾说,比喻像是一种很小的魔法,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场景重叠在一起,一个句子就出现了两种画面。通过一层层微型的场景嵌套,拐卖受害者的经历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相连,仿佛每一种痛苦都有了名字。
童话改编的创作传统
张天翼在创作谈中写道,格林童话中,“主角统统不可爱,公主的脑子也和雪地一样空白,王子爱上一具死尸,还要运回去同吃同住,简直变态。跟七个男人同住一屋,给他们做饭洗衣服(很可能包括内裤袜子),每天还要亲吻七个秃顶,这是我童年心中最恐怖恶心的情节。”作者自小对男性书写的童话的反感与质疑成为《白雪》的创作源头,她借小花梅的拐卖案件,将一个有思想有感受的灵魂塞入白雪公主这个头脑空空的真善美化身中,打破了格林童话中的男性叙事。当歌颂真善美的童话世界与一起有关拐卖与性剥削的恐怖事件挂钩时,张天翼完成了对童话的反向度写作。某种程度上,这一题材的改编也构成一种反讽,如同白雪遭到性侵害时,施害者说,“到时候你就,跟我,好好过,我一辈子,宠你,拿你,当,公主,一样。”
格林童话中,白雪公主的形象几乎抽象为对比强烈的色彩,白如雪的肌肤、黑亮如乌木的头发、红润如血的气色。张天翼续写了格林童话中的色彩,不同的是,《白雪》中的色彩变得具体生动,常与食物、衣物等日常所见之物挂钩,饱含温度与情感。张天翼曾说,他人或将时间地点当做坐标,而她将色彩、光线作为自己的锚点。故事开头,白色是牛奶、米饭,是婴儿的围兜、毛线裙、连脚袜,白色也是即将离世的母亲的面色、氧气罩里一次次造出的雾气,是医生的袍子、葬礼上的麻衣和布条,粉白、奶白、藕白、肥白、灰白、蜡白,暖色与冷色的白混杂在一起,拼凑出主人公的生活。拐卖则是一把锐利的刀,将往日的白雪变成尸骸,将色彩拦腰截断,只剩下矮人之家猪肝红、淤血一般的门、回忆里期盼中洁净的白......
张天翼注重小说技法,兼具文笔和故事结构搭建,她自称一位手艺人,写小说如同摊煎饼。在检索张天翼的信息时,上个年代的同名男作家也常被提及,其经典童话作品《宝葫芦的秘密》是许多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像是某种巧合,两个张天翼都在童话这一体裁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作为一位青年写作者,张天翼用童话嫁接现实,擅长描写细微的女性处境。在她2021年出版的小说集《性盲症患者的爱情》中,同样改编自格林童话的《睡美人的梦》借用了原本的童话背景,但睡美人不再是原著中被动等待救赎的形象,反而以第一人称讲述者的视角敏锐地观察着整个世界,并引导冒险者帮助自己与家人打破诅咒。
《白雪》作为张天翼童话改编系列的最后一篇,在童话元素与现实的融合上更加熟练,在人物形象和故事创作上更具颠覆性。其语言风格相比《性盲症患者的爱情》中浓烈得近乎赤裸的情感表达,变得沉静内敛,但究其内核,仍然出于本能。
张天翼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谈到女性处境,她认为自己是个软弱的人,不勇敢也不果断。她关注各种社会议题,“知道自己应该有所反应,应该愤怒,但我什么都没有做。”或许正是感受到女性之间相连的命运,以及身体里无处放置的愤怒,她将自由作为自己的创作母体,书写一个又一个被禁锢被束缚的女性故事。
对审查的突破
张天翼在创作谈中讲到,想写这个故事,是为了纪念前几年新闻里一位被铁链锁在小黑屋里的姑娘,为了纪念她的不能被提起。受制于信息封锁、审查与禁言,我们很难看到铁链女事件的详尽报道以及相关讨论,更多的是残留在互联网各处的零碎信息,无法确定真假。这一切真真假假的信息借助小说的载体、借用白雪公主这一经典意向,重新落回纸面。作者透过想象与考据,用第一人称视角展现了一个普通女孩如何轻易地陷入被剥削的处境,被扣上“疯女人”的帽子,一步步走向精神崩溃的濒死境地。在反复强调故事的虚构性中,文本获得了另一种历史性的真实感。
移植故事背景,书写敏感的社会新闻事件,以便绕过审查,这种寓言式的写作技巧被20世纪犹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称作“隐微写作”。施特劳斯在其著作《迫害与写作艺术》中提到,隐微写作明显是隐喻性的,带有构思晦涩、矛盾、怪异、迂回、暗示、提示、象征、双关等等特点,通常诞生于专制、不自由的社会背景下,它只向那些值得信赖的聪明读者开放。
古今中外,为躲避审查与被迫害的风险,很多文本不可避免地带有隐蔽的方式、形式和风格。不同的修辞方式与虚构手段,皆可成为隐蔽的对抗方式。例如一年多前的虚构作品《德黑兰狱中来信》,作者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移植在伊朗的背景下,骗过了审查者。施特劳斯认为,迫害是偶然的,它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压力的少见情况。但“迫害”可以引申为一系列潜在的社会反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在压力和自我审查,这会限制写作者的自由表达。事实上,很难想象一个社会不限制作家的言论、表达条件和其写作对象。当这些限制与良心、责任感、不得不说出口的痛苦发生冲突时,会推动写作者去找寻与审查者斡旋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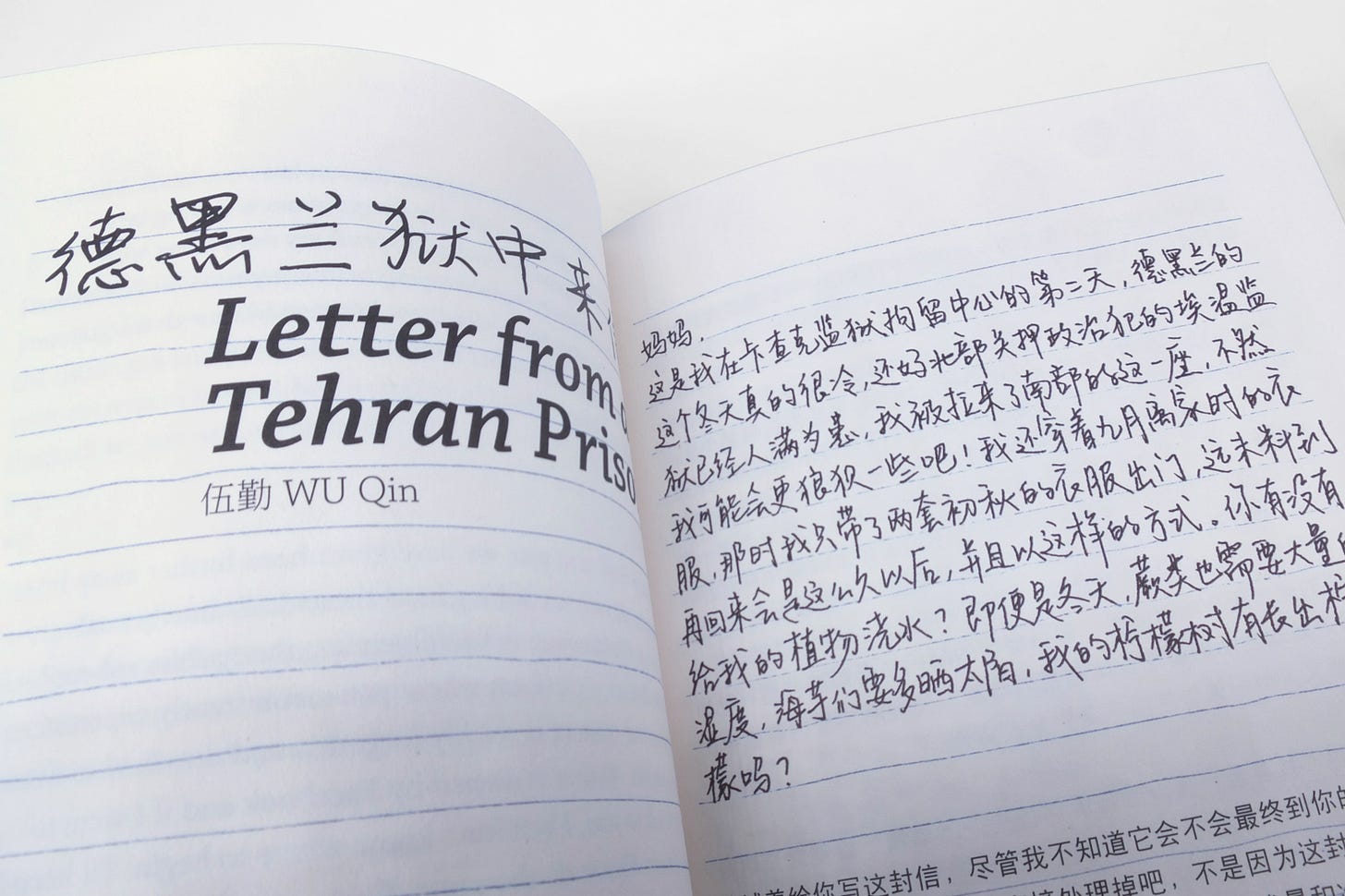
只是,借用寓言式的写作手法并不能让审查压力完全消失。张天翼谈到,书写小花梅的故事,预设它可能发不出来。拿给一位相熟的杂志编辑,编辑也觉得很危险。即便全然抹去了“铁链”与“梅花”的字眼,删掉了虽远不如现实惊悚、但搁在纸面上已足够阴暗的几个情节,仍有无法过审的风险。从结果来看,张天翼的这一书写方式实现了对审查的部分突破,这也构成了小说价值的一部分。这个故事能够得见天日,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转发分享、推荐订阅!如果你也关注农村精障女性、人口贩运、性别暴力、残障正义等议题,希望加入我们、投稿、提供新闻线索、请求内容授权、交流想法等,可以发送邮件至:nomorechained@proton.me。